《探秘苏东坡》| 学子东坡④:好马遇伯乐
来源: 责任编辑:蒋萍 2019年12月14 12:08:2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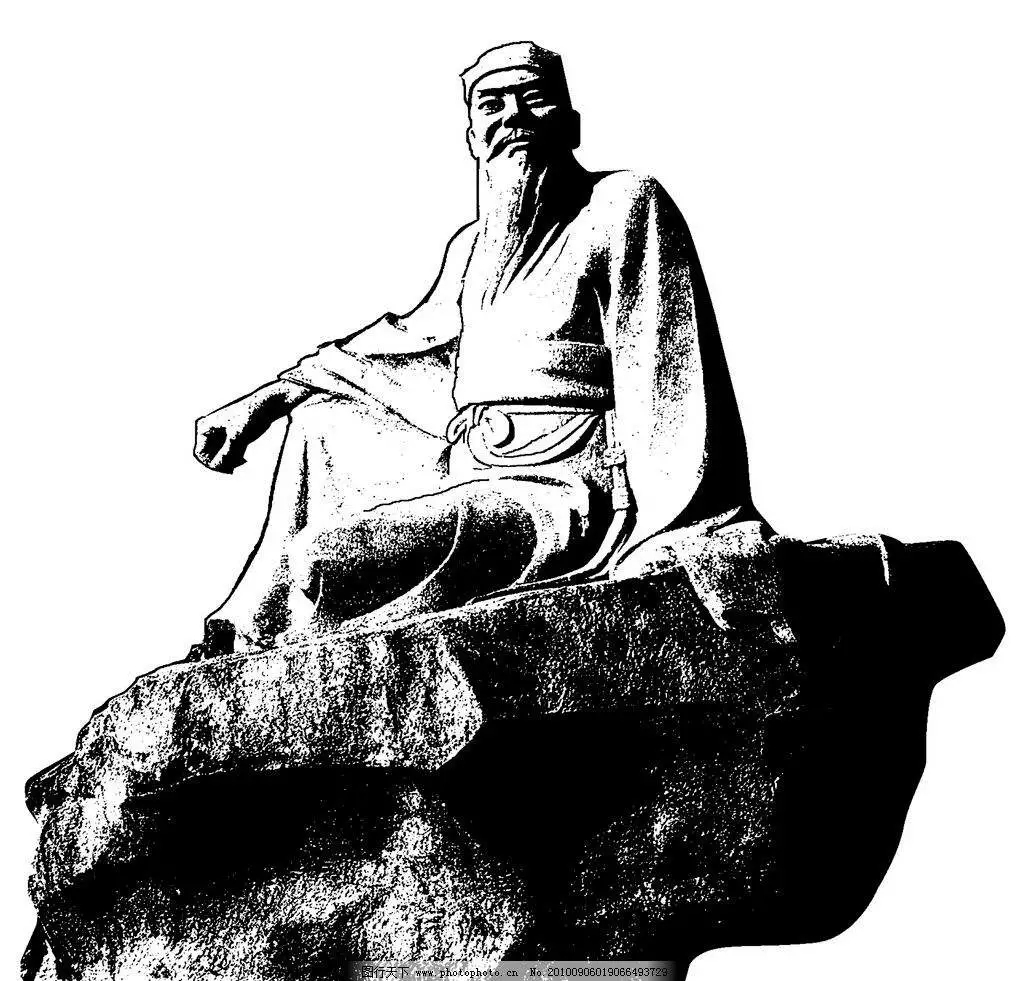
苏轼读书,渐入佳境。苏洵某日出了个题目:《夏侯太初论》,命苏轼作文。苏轼文中有这么一句,“人能碎千金之璧,不能无失声于破釜;能搏猛虎,不能无变色与蜂虿。”这是直指人性的话,比喻一个人能历经大风大浪面不改色,却常常会在阴沟里翻船。小毛孩子能做出这样的句子,实在令人佩服,苏洵得意极了,大加赞赏,逢人便夸。后来苏轼做《黠鼠赋》,教育自己的孩子,也把这得意的句子用了进去。
眉山学者刘巨,字微之,在城西寿昌院办了个学堂。苏洵把两个孩子送了进去,苏轼当时大约十二岁,算是念初中吧。学堂里的同学们爱玩一种文字游戏,几个小朋友坐在一起,出个题目,每人轮流做一两句诗,再串起来便成一首完整的诗。一日,天降大雨,苏轼兄弟与另外两个小朋友听雨声观庭松,觉得颇有趣,便开始作诗。前两句“庭松偃仰如醉”、“夏雨凄凉似秋”,苏轼接第三句“有客高吟拥鼻”,并不见得高明,大约是做着玩的。最后轮到苏辙,他还不到10岁,只道:“无人共吃馒头”,笑倒一片人。
苏轼兄弟在刘微之那儿念了大约三年书,学有所成。那刘微之爱作诗,一次做了一首咏鹭鸶的诗,最后两句是“渔人忽惊起,雪片逐风斜。”雪片代指雪白的鹭鸶,“逐风斜”,很凄美的感觉。刘微之摇头晃脑念得挺得意,等着课堂上的几十个学生拍巴巴掌。苏轼却站起来说:“先生的诗好是好,但我怀疑最后两句没有归宿,不如改为‘雪片落蒹葭’,好不好?”蒹葭即芦苇,“落蒹葭”,给了那鹭鸶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学生修改了老师的佳句,刘微之愣住了,一如当年的张易简。大约他心里也称赞,但不便过分表露,只道:“吾,非若师也!”就是我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了。
关于“逐风斜”和“落蒹葭”究竟哪句更好?历代学者说法不一。笔者猜测,苏轼从小接受母亲程夫人的情感教育,萌发出一颗仁爱之心。比起那凄美的意境,小小鹭鸶的命运更能引起苏轼的关注。苏轼一生以天下苍生为念,将博爱二字诠释到极致,或许在他小时候就形成了这种苗头。
苏轼读书,除那些必读的经典之外,酷爱贾谊、陆贽的文章,都是不尚空言,侧重实用。这可能也是受他父亲的影响,苏洵就最烦那种华而不实的“声韵之律”。苏轼离开寿昌院后又自学了几年,其文章渐成风格。敏锐的洞察力,内含旺盛的气势,并且言之有物,不唱高调。文风似孟子,论事则如陆贽。
“钗于奁内待时飞”,弱冠之年的苏轼也将参加科举,踏上仕途。
1054年,苏轼与青神人王弗结了婚,当时苏轼大约18岁,而王弗15岁左右。不久后,苏辙也同史氏完婚,一个17岁,一个15岁。现在看来,当然这是早婚了,不过在当时是很平常的。并且兄弟二人将要赴京赶考,先在家完了婚大约也是父母的意思。
同样是1054年,礼部侍郎张方平出知益州,即成都。这张方平是个奇人,喝酒百杯不醉。他自小阅读经史,过目不忘,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。并且他礼贤下士,好挖掘乡野遗贤,来蜀之前,便了解到蜀中有苏洵这样的人物,很想见一见。上任成都后,苏洵来拜访他,两人气味相投,聊得很欢。张方平辟了间屋子留苏洵住下,并上书朝廷,保荐苏洵为成都学官。怎奈苏洵官运不佳,朝廷那边始终没动静,搞得他相当郁闷。
终究是做父亲的,都盼着孩子能有出息。自己的事暂且搁下,苏洵为两个孩子谋起了前程,他带了苏轼兄弟同赴成都。见了苏家二子,张方平喜欢的不行,尤其是苏轼,惊为“天上的麒麟”。苏辙只有17岁,但也不错,张方平以“国士之礼”接待二人,规格甚高。眉山三苏,与益州太守共聚一处,大口吃肉,大口喝酒,大谈天下大事,快活得很。
这事儿很快便传开了,苏轼与苏辙在成都也成了名人。两位年轻公子,不单生的高大帅气,并且风华正茂,是太守府里的贵客。兄弟二人一同骑马出游,惹得成都姑娘们芳心摇动,投去火辣辣的目光。大约苏轼与苏辙也挺享受这种气氛,但也仅限于此。他们在前面自顾自地逍遥,任那背后的少女们窃窃私语:“若能嫁给这二人,那才叫美呢。”旁人提醒:“大苏小苏都已经娶过了。”少女们叹气:“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嫁给二苏呢?能有这等福分,命好!命好!”多年之后,苏辙作诗感慨:“成都多游士,投谒密如栉。纷然众人中,顾我好颜色。”
苏洵琢磨着,打算先让二子先在本地参加乡试。而张方平认为这是大材小用,建议直接赴京赶考,怕这父子三人或有麻烦,他还硬着头皮给翰林学士欧阳修写了封介绍信,推荐三苏。其实张方平与欧阳修私交并不好,二人因政治立场不同,曾发生过激烈摩擦,搞得几乎绝交。写这样一封介绍信是要冒风险的,万一欧阳修计较前嫌,那不就坏了三苏的前程?或许张方平有过剧烈的思想斗争,但他心里也清楚,以欧阳修的风度,不大可能干这种小人之事。事实正是如此,在京城,欧阳修对三苏的大力推举,比张方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两位北宋大人物劲往一处使,日后也以此为契机,泯去了彼此的多年恩怨。
1056年三月,三苏父子启程,骑马北上,到陕西马累死了,改骑驴子。一路上备尝艰辛又饱览风物,历时两个多月,行程一千七百里,终于到了京城。(文/刘寅)



